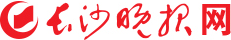亚坤夜读丨工地上的儿子(有声)

儿子大学毕业后,便从长沙到湘江源头一大坝工地任工程监理员。工地是啥模样?我决定去看看。
驾车到了工地附近,儿子来镇上接我们。他头发不像以前老遮搭着额头,人精神多了,男人多了。看来,将男孩打造成男人的最佳场所是工地,而其成熟的速成方式首推泥一脚水一脚的生活。
进入工地的路,大型工程车来回碾压,坑坑洼洼,我的小车被蹂躏得摇过来晃过去。尺多厚的水泥路面被碾成无规律可循的块状,高高翘起,“横刀立马”给我下马威。路上石坷垃,冷不防顶着底盘,落差有点大,时时担心被架空,我倒吸阵阵凉气。
峰峦层叠,不敢远视,车到跟前才发现峡谷下面便是大坝工地。混凝土底座已筑几十米高了,如张开刚劲的双臂,挽起两端山峦。挖掘机剖开两边山坡,狠狠扎进山的胸膛。裸露的山体呈现黑灰色,有点像云朵投下的阴影。
闺藏深山峡谷中的大坝,左边是工地,稀稀拉拉停着红色工程车,工人们正在午休。右边山坡上有工棚、楼房、平房,依山而建。那钢结构工棚很高、很扎实,挨着大坝,是汽修厂,前坪停满了能装百来吨的大型工程车。毗邻汽修厂的是个大型独立院子,两层楼,地势低一点,门上挂着某某施工公司的招牌,国家一级企业。再往下的独栋楼房挂有医务室、社区招牌,房子有点岁月,显然是以前村部驻地。最西头是监理公司,两层楼,蓝白色的活动板房建在半山腰上,也是独立院子,锁着门。
天很蓝,云很白,连绵起伏的青山被太阳染成金色。鸟儿稀稀拉拉地唱着午曲,远远近近,此起彼伏,高昂的、欢快的,互相呼应。森林氧吧把太阳的热力吸收,释放的氧离子充盈着整个山谷,我们吐故纳新,将城市喧嚣中浸染的世俗和浮躁涤尘去垢。天地间秀色美景,我心胸豁然开朗,享受着山水间的诗意,体味着风摇翠竹的情调,在峻岭溪水中揽欢,伴瑶池仙境飘渺入目,我多么想久留。
儿子说这个小山冲,夏天比长沙凉爽,冬天比长沙温暖。清凉的风,掠过坝底那条清澈的小溪,扇动着树叶婆娑,迎面扑来丝丝凉意,我赶快双手捂住肚子上的衣服。
工地上不安全,几十亿的大工程只能远眺。工程车辆开始从午休中醒来,佝偻着身子缓慢地爬上陡坡,喘着粗气荡起滚滚灰尘,地动山摇起来。坝上,高耸云天的塔吊,轻车熟路地转过身子,将货物送达目的地。坝底,挖掘机开始轰鸣,刚健的臂膀钻进沙石中,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工地,见不到以前修水库那种人山人海、喇叭高歌鼓劲的场景,除了机器轰鸣就是车辆穿梭,看似无序却有序。儿子和其他水电建设者一样,在山中度过了百多个烟雨朦胧的日子。他已融入到工地中,下班后也常去县城打球,和县水利局、工程公司等球队对垒。他说脚踝处又受伤了,我不想阻止他这种爱好,也许这是工程人员的全部社交活动。
儿子主要的工作是旁站、巡视,平行检查,每天跟着师傅“翻山越岭”做好安全监理记录。他指着对面的山头说,建成的大坝高度就在指示牌那里,比东江湖大坝还高。
儿子那专业大多数学生必然走上工地。本可以在长沙找到工作,不签三方协议,待遇低,他放弃了。没出身豪门,没上名牌大学,他离开大城市来到山中。
突然想起作家毕淑敏,当兵前享受北京最好的生活。来到西藏部队,海拔五千米的雪山中,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,她同男人一样,负重几十公斤,徒步行军于皑皑雪原中。攀越壁立的冰坂时,受不了非人的苦难,她曾热切渴望死亡。后来她才明白,这是青春生命本能在反抗。雪原中度过十一年,贮藏太多种子,萌发便不可收拾,我喜欢翻翻她的作品。
山中苦中寻乐,水中磨砺前行,我无法判断这苦行僧日子,是不是激情。我一直强调专业的重要性,却无法说清楚这决定是否正确。也许从来没有最正确的选择,我们能做的,不过是努力把每个选择变正确。年轻人就该在心中筑座大坝,不断提高水位,直到落差能与人生目标匹配,便没辜负那段经历。通往成功的路,总是在施工,落在儿子身上是座大山,也可能是粒尘埃。
看过工地后,我心中有了“想像点”,山中寂寞、艰辛,也有风景。两个月来,想他时,就浮现那个画面。蓦然回首,并非每人都能看到灯火阑珊的那个场景,却印在我心中。

>>我要举报